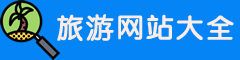|
soho·女王·金融城·泰晤士河 ——伦敦不倦之旅 ‘when a man is
soho 去看soho,是为了体验伦敦的快乐。 soho是个容易引发歧义的名词,soho一族是small office & home office(自由职业者)的意思,纽约的soho区是指south of houston street(休斯顿街以南),而伦敦的soho区则是位于伦敦心脏部位的一片区域,这里的soho文字本身没有任何意思,只是据说直到十七世纪时,soho区还是伦敦的一个猎场,soho是狩猎时人们吆喝的声音。今天的soho是各式酒吧、餐馆,时装店、内衣店的聚集地,周围还围绕着一些剧院和电影院,被誉为世界九大夜生活区之一。 华灯初上是soho的集结号,慕名而来的远方游客、意气风发的商界精英或失意疲惫的工薪一族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soho的夜生活开始渐入佳境。作为体验soho夜生活的入门,soho最繁华地段沃德街的酒吧是个不错的选择。酒吧中,客人不管来自何方,脱去了西服职装,淡化了身份职位,暂时远离了重大的事情,徜徉于音乐和美酒之间,随意和释放成为了不二的主题。经常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商界精英,可以在随着音乐轻动的步点中寻回已经陌生了的对陆地的感觉;整天在职场办公室奔忙劳碌的白领阶层,白天被信息化时代抽象符号数字充斥着的头脑,可能会在呷下一杯冰冻啤酒之后,恢复对具体生活的感觉,激发新的工作热情;甚至,日复一日缠身于一个又一个法案争辩中的政客,也可以在无心快语的聊天中,恢复寻常人的判断或直觉,在第二天的争论中,抛开严谨的法理推断和似是而非的条条框框,作出最接近正确的选择;即使是游客,在经典场景和厚重历史中浸泡了一整天之后,也很有需要在soho的音乐、啤酒和闲聊中舒缓一下,释放一些审美疲劳,积聚一点新的激情。在soho广场旁边,有一间马克思的故居。或许马克思白天在大英阅览室读书写作累了,晚上也需要在soho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酝酿新的创作灵感。而莫扎特小时候是也曾在在这里居住,可能他的小夜曲中就包含着孩提时代某个夜晚窗外飘来的街头艺人演奏的一段旋律。 世界上大多数的都市可能都有类似soho的这么一个地方,但伦敦soho特别之处在于:置身soho,反差的感觉特别强烈,一切都似乎发生了颠覆。作为欧洲主流文化的起源地,伦敦给人的印象是经典、庄重,甚至刻板,而soho给人的印象却是反主流,酒吧有传统清吧也有光怪陆离的同志吧,书店一楼摆卖着经典名著楼上却堆满着五花八门的情色书刊,戏院门口的海报女主角迢迢淑女,对门内衣店的模特女郎却是大胆暴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soho当年它曾以色情业闻名,但如今的soho情色指数是有限度的,传统色情业已经从这里消失。在soho,即使是在一家传统清吧,颠覆的感觉也都一点不会少。酒吧的装饰混合着古典的华丽和现代工业的冷酷、夹杂着颓废和张扬的元素,颠覆着人的时空感觉。伦敦人平常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甚至刻板,而到了酒吧,这种印象却被颠覆了。拿着酒杯听着音乐的伦敦人像上海人一样能侃,遇上陌生人也不例外。酒精可能是全球通用的沟通润滑剂,文化隔阂被轻易敲破,甚至语言障碍也不复存在,杯酒下去英语会说得特别顺溜,和伦敦人侃大山跟和老朋友把酒言欢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喝着各种颜色的酒,谈着各种颜色的笑话。英方吹嘘贝克汉姆场上场外功夫如何了得,中方冷笑一声:贝克汉姆上上下下哪里能跟姚明比?什么尺寸什么重量级?英方说中国人居然能容忍吃狗肉,太荒谬!中方说英国人居然能容忍整天就吃薯条炸鱼,更荒谬!英方说尽管中国有数千年的皇朝历史,但时至今日仍活现着皇室的却是白金汉宫,中方说白金汉宫放到故宫去充其量就是间太监睡的房子,情急之下太监被地解释成了a ma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his body 伦敦是全世界消费最昂贵的城市之一,但soho 酒吧的消费却说不上昂贵,一两镑一杯啤酒,三五知己每人请上一轮,也就十镑八镑。花不大的代价,在音乐的起伏中,在啤酒泡沫的升腾中,身体的劳累、心中的郁结、今天的无奈、明日的彷徨,或徐徐地挥发,或慢慢地沉淀,新的希望又再升起。有soho 这么一个好地方,伦敦人是幸福的。有soho 这么一个好地方却不用来soho的伦敦人是更幸福的,他们下班了匆匆回家,回去享受平淡而幸福的相厮相守,一切的劳累和不快都在家的港湾中被抚平,比起用酒精麻醉的幸福,他们的幸福来得更真实。 soho是夜伦敦的乐园,而科芬园则是伦敦白天的乐园。科芬园是伦敦最具规模的跳蚤市场,历史上曾是修道院花园,后来成为伦敦最重要的青果花卉市场,大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就是在科芬园与公爵相识。现在的科芬园已演变成为各种商店、餐馆、咖啡座、市场摊档、精品店及街头艺术家们表演的聚集地。步出科芬园地铁站,一种伦敦街头少有的热闹生气让人为之一振,熙熙攘攘的人流,离奇古怪的真人雕塑或行为艺术,情绪马上被调动起来。再往里走,是一排排布置和摆设都很有艺术气息的小商店,有着各式各样的小玩意,走在里面感觉像逛商店也像参观艺术长廊。在商店里看累了走累了,在商店之间的茶座歇歇,听听街头艺术家的小提琴或色时风,这里的鸽子和游人一样放松,不时飞过来凑热闹,叼吃桌面上散落的点心碎末。陪着鸽子吃过点心,继续逛商店摊档,然后又继续到市场二楼的露天咖啡座休歇,晒着暖暖阳光,喝着浓浓咖啡,看着街头的表演,街头四面八方的表演形式多样,偶尔会失手的杂技,偶尔会露馅的魔术,现代版的卓别林,夸张版的憨豆,只要愿意,就可以一路看下去开心下去。在科芬园看街头表演,看客是快乐的,而表演者看上去更快乐。在科芬园,商业和艺术、雅和俗、生活和工作的界线变模糊,快乐成为了一切的共同要义。
女 王 去看女王,是为了浏览伦敦的历史。 看女王一般都从看白金汉宫卫兵换岗开始。白金汉宫从十九世纪开始成为王室的宫殿,现在局部开放给游客参观。白金汉宫的屋顶如果悬挂着王室旗,就表示女王在家,不过无论在家与否,游客都不可能遇上女王。换岗仪式春夏季每天十一点半进行,秋冬季则是隔天举行。看换岗仪式感觉和看天安门升降旗仪式差不多,总是大早就堆满人了,换岗仪式先是当班的卫兵在院子内进行步操,然后撤出,下一班卫兵进驻,卫兵穿着红色的礼仪装,戴着高高的熊皮帽子,还有乐队伴随,场面甚为热闹。实际上卫兵的角色已不再是真正的卫兵,真正的警卫工作更多是由安保部门承担了,卫兵只是一种象征、一种仪式,就像女王基本和国家权力无关,只是一种象征而已。不过如果不是各种各样美仑美奂的王家礼仪还保存着,英国的业一定会大受影响。 真正能在白金汉宫门前亲眼看到女王的只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比如她的官方生日。按照王室的规定,女王的官方生日定在六月的某个周六。生日当天上午,王家卫兵在白金汉宫门前的林荫大道五步一岗列开,游客居民拥挤在大道两旁等候女王的车队游行经过。十点钟,先是步兵、骑兵、乐队方阵开道,然后是王室成员依次走过,一般成员坐的是汽车,主要成员才有资格坐马车。女王的马车最后出来,街头民众的欢呼声自然也最热烈,“queen, queen”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场面十分热烈,美中不足的是空气中弥漫着骑兵卫队走过留下的马粪味。坐在马车上的女王感觉估计一定不错,这地球上没几个人过生日能像她这样风光了。女王的车队游行到骑兵卫队的操场,然后在那里进行阅兵仪式,英文叫trooping the colour, 大概就是和分列式差不多了。女王阅兵礼后返回白金汉宫还有一个空中阅兵仪式,空军的飞机喷射着不同的颜色在王宫上空列队飞过。英国王家空军(royal air force)简称raf,却被人戏称为是run away first(逃跑第一)。 女王官方生日顾名思义是官方的,当然就不是她真正的生日。英国王室原先并没有官方生日这一说法,只是从某个国王开始,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十二月寒冷的冬天,不适宜举行盛大的公众庆贺仪式,于是创设官方生日的规矩,以确保国王能在温暖阳光的日子接受子民的欢呼祝贺。女王的真正生日是4月21日,一般生日当天她会和家人朋友在温莎堡度过。4月的伦敦还有点冷,甚至还在下雪。要想每年都拥有一个温暖的生日?重要的不是出生在哪个季节,重要的是你是否永远在某人心中比女王还重要。 国会大厦是女王参政的地方,女王一年会到国会大厦开三两次会。国会大厦曾是王室的居所,后来随着国王对政治的渐行渐远搬出去了,而国会大厦也于十九世纪中叶被大火毁掉后重建。国会大厦是世界上最大的哥德式建筑物之一,要领略它的恢弘气派必须从泰晤士河南岸看过来,整座大厦用灰黄色石块建造, 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强烈的古典美。要了解国会大厦的内部风貌,则需要购买参观的门票。进入国会的中央大厅,抬头是高高的穹顶,空间实在是太大了,亮着灯,大厅里却是暗暗的。大厦以中央大厅为界,南侧是上议院,北侧是下议院,大笨钟伫立在北端近百米高的钟楼上。 英国的议会是两院三方。议会会议大厅中女王的座位高高在上,但女王却是三方中最没有权力的一方,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和理论上的政府首脑。据介绍,女王来开会时,王冠和女王分乘两辆马车从白金汉宫来到国会大厦,到达后,女王穿上长袍,戴上王冠,然后端坐于王座之上,也不知道人们更看重的是作为国之器者的王冠,还是戴着王冠的女王。上议院是世袭的,上下议院如果一起开会是在上议院大厅开的,上议院议员是有座位的,但只有部分权力。下议院是选举产生的,虽然到上议院开会时得站着,却拥有最广泛的权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权力体制起源于约八百年前温莎堡草地上的一卷羊皮纸。近八百年前的一个清晨,几十个英国贵族带着一卷写在羊皮纸上的请愿书来到国王居住的温莎堡,羊皮卷上写着若干条限制国王“不得这样、不得那样”的条款,有些条款现在看来只是鸡皮蒜事,但却明确了一条大原则:法律高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尽管当时的国王对请愿书有点皱眉头,却很懂得审时度势作出妥协,而贵族们亦很懂得适时退让,于是,数个世纪走过,天翻地覆,世事变迁,今日的英国却依然有王室也有议会,王室依然风光着她的风光,议会也民主着她的民主,而国民,也享有着可能比世界上一些有议会没国王、或没议会有国室的国家更自由幸福的生活。 议会大厦对面是西敏寺,西敏寺是一座教堂,但更是英国王室的象征。英国的 西敏寺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归宿地,还有一个“诗人之隅”。诗人之隅其实不仅仅包括诗人,还有作家、作曲家。最早归宿在此的,是英国诗歌的鼻祖乔叟。而大名鼎鼎莎士比亚,在辞世百年之后也在寺中谋得一方石碑供后人膜拜,他至今安息在故乡雅芳河畔之斯特拉福的泥土中。其他立碑者,略晓一二的还有雪莱、拜伦,霍普金斯、白朗宁、狄更斯等大作家大诗人,而更多的是超出了本人学识之外的名字。帝王将相选择死后与诗人作家为邻,不知是为了让诗人作家继续歌颂他们生前的丰功伟业,或继续用诗句名作温暖天国中的落寞? 哈罗德百货也是了解女王生活的好去处,尽管今天的哈罗德和女王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却可以对女王用的瓢盆碗碟大致有个感性认识。哈罗德百货是伦敦骑士桥上一家有着百多年历史的老牌百货,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富豪法耶兹于斥资 6亿英镑斥资收购。英国王室曾是哈罗德的忠实顾客,在法耶兹的儿子与戴安娜王妃出双入对并在车祸中丧生的事故发生后,因为法耶兹指控英国情报部门和菲利普亲王参与了对戴安娜的谋杀,哈罗德失去了英国王室的惠顾垂青,人们再也看不到哈罗德百货的工作人员穿着传统服装赶着马车给白金汉宫送货了。哈罗德里面的装修极尽奢华,据说法耶兹前前后后投了3亿英镑进去。三楼的“埃及厅”装饰着狮身人面像和埃及壁画,不经意还以为到了埃及。而据报道说法耶兹甚至语出惊人自己死后要将尸身制成木乃伊, 在哈罗德楼顶修一座大钟, 用自己的尸身当指针给伦敦人报时。到哈罗德购物需要讲究礼仪,穿拖鞋不受欢迎,嚼着口香糖不受欢迎,背双肩包得改用手拎着。哈罗德百货卖的不是一般的百货,普通商店能见到的尊贵名牌货品, 在哈罗德只能算大路货色,哈罗德卖的是别处看不到的商品:10万镑一瓶的香水、50万镑一条的裙子、100万英镑一双的鞋子。哈罗德的经营哲学是:“任何地方任何人需要的任何物件”,只要你住在离地球不太远的地方,只要你需要的还没超出银河系,只要你还能支付账单, 哈罗德都能为你办到。不过,即使在大减价的日子,普通顾客就算把家里的房子卖掉,来到哈罗德也买不了几样东西,最实惠的还是花上一英镑,
金 融 城 去看金融城,是为了领略伦敦的繁荣。 金融城的英文名字是the 地铁是伦敦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伦敦地铁有12条地铁线在六个区里纵横交错,伦敦地铁(london underground)直译就是“地下的东西”,似乎说到伦敦地下,就必然是在说地铁,可见地铁在伦敦的江湖地位,不过似乎伦敦人口头更多用tube(管道)来称呼地铁。伦敦地铁的每条都有自己的名字,如“皮卡地里线”、“维多利亚线”、“朱比利线”,但伦敦人更喜欢线路图上的颜色标识来指代线路:比如“坐红线去上班”,“坐蓝线去购物”之类。有些站点几条线路同时交汇,结构特别复杂,自动扶梯又高又陡,向下走时有畏高症的都不敢直看前方,好在两旁挂满了不断更新精彩有趣的广告海报。伦敦是世界上最早有地铁的城市,一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新旧线路差别很大,有像八十年代京广线一样破旧的,也有像广州地铁三四路线一样新净的。伦敦的地铁票种类繁多,次票、日票、周票,高峰期票、非高峰期票,由一区到六区不同范围的票。对于普通游客,较合适的是非高峰期一二区通用日票或周票,日票约5镑,周票约22镑,一二区基本包括了伦敦核心部分,一般的旅游不会超出此范围,非高峰期日票就是除工作日早上9点半前上班高峰期不能使用外全天可以多次乘搭地铁或巴士的,省点钱且有理由睡懒觉当然是很好的选择。 金融城最初只是商人们聚在一起喝咖啡、谈生意的地方,逐渐地运输业、保险业、银行业在这里发展起来,成为英国经济活动的中心。现在,作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只有区区1平方英里、居民人数不足1万人的金融城却有数百家财富500强公司和外国银行在此营业,有30多万员工在此上班,每天外汇交易量占全球的三成多,每天场外衍生金融产品交易额占全球的四成多,创造着英国近4%的gdp。 金融城大多数的建筑都保持着古旧的外貌,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外表也极为普通。英格兰银行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富有的银行,因为它是全球最昂贵的货币英镑的发钞行,而且有报道说,为保证市面上纸币光鲜地流通,英镑纸币在市场流通期限仅10个月,银行不断推出新币,而回收的旧币则由银行烧掉,所以有人戏称,英格兰银行富有到在冬天里是靠烧英镑来取暖的。 伦敦金融城有两座建筑物格外抢眼。一座是瑞士再保险公司总部大楼,40多层高,外形像一个等待发射升空的火箭,据说这幢大楼使用了超过1万吨的钢材,其外表覆盖的玻璃相当于5个足球场的面积。另一座是劳埃德保险大厦,整个建筑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大工厂,外表是不锈钢的,各种金属管道裸露在外纵横顺交错着,据说,这是打破黑箱裸露一切的保险理念的艺术再现。劳埃德其实并不是保险公司,而是世界最大的保险交易市场,作用有点类似证券交易所。据介绍,劳埃德旧传统与新科技高度融合,业务员可以通过现代信息系统,对在劳埃德买了保险的全世界数万艘远洋商船的活动了如指掌,而一旦有船只出险,业务员还会用十七世纪的鹅毛笔将其手工登记入册。 走进金融城的一条胡同,来到“牙卖加咖咖店”,据称是伦敦城历史上第一家的咖咖店。坐在可能曾完成过世界第一宗金融交易的座位,咖啡的热气徐徐升起,关于金融和历史的一些随想也徐徐展开。伦敦金融市场跌宕起伏数百载,故事太多,无法不好好想一想;伦敦城走出的经济学圣殿级人物太多,如雷贯耳,不能不好好想一想。 伦敦金融城的金融衍生品种之多,可能即使是置身其中的从业者也无法一一道来。在数不胜数的即期远期、期货期权、掉期互换交易品种中,有人在卖出风险,锁定收益,有人在买进风险,博取收益,有人在复杂的对冲组合小狭缝中谋求大利益,产品形态百异,众人心态百异。然而,顺着金融发展史的长河往回看一下,无论利率汇率、股票债券,最原始的形态大致都可以归结为简单的借贷关系。再往回看一点,借贷其实和市场无关,不过是亲朋好友在助人之心、同情心等种种“利他心”支配下作出的行为,但“利他心”显然无法市场化,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资本市场的要求,无法带来金融市场的繁荣。于是,以“利己心”为原动力的借贷出现了,借贷被市场化了,社会快速发展了,金融市场高度繁荣了。 或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是透过伦敦城繁复的市场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他的《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基石不是某个经济学概念,不是某条供求曲线,而是人性。《国富论》认为利己心乃人的天性,是经济的原动力,是经济交换的基础,是研究经济学的起点。相比于人性,公式、曲线甚至最复杂的理论都是简单的。如果公式可以解决问题,擅长发现和运用公式的牛顿就不会伦敦股票市场“南海泡沫”事件中中招,高位套牢,就不会发出“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的感慨,其实他自己也疯狂了。如果理论造诣可以战胜“看不见的手”,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的现代西方经济学里程碑式人物凯恩斯,就不会一度因卖空马克破产,然后再度因股票交易险些破产,只是因考虑到再次破产可能会损害他作为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声誉,不得不主动退出投机行列。凯恩斯的投资哲学是“如果共有100幅候选美女照片,由公众从中选出4人,人们并不投票给他认为是最美的人,而是选择他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最美的人”,理论不错,可惜凯恩斯对人性认识不够深刻,他的审美观总不够大众化。或许证券交易师之子大卫李嘉图在两代人的市场经历中明察到了人性博弈的无常,在买卖英国国债赚了第一桶金后,转向做学问,研究出了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了现代贸易理论的奠基人。或许写出了教科书式《经济学原理》的马歇尔大师深谙自己可以描述出各种各样的供求曲线、弹性系数、边际递升递减,却无法把握由人性支配着的市场轨迹,因而一直和市场保持着距离。 时代在进步,信息技术在日新月异,分析工具在推陈出新,不变的却是人性。于是,在信息技术和分析工具的帮助下,人们更容易收集到需要的数据信息,更容易分析出曲线的技术走向,只是依然无法读懂屏幕闪烁的数字或k线背后隐藏着的人性密码,于是历史总在重复,市场总在常涨常落,大多数人总在无奈中祈求谁能“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纷扰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利己心”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基础概念,但亚当斯密对人性的认识却常常为人所曲解,人们往往会忘记了他的《道德情操论》,一部写在《国富论》之前、论述“利他心”的鸿篇巨作。亚当斯密倡导的是伦理上的利他性和经济上的利己性两者平衡结合,以增加个人财富和社会福利。可惜,“看不见的手”遮断了许多人的视线,亚当斯密期待的人性黄金平衡点总找不到移动的方向。 牙卖加咖咖喝了一杯又一杯,随想想了一段又一段,有点累,往店外望一望,望见了远处飘落的梧桐叶,望见了街头走过的十指紧扣的一对小情侣。突然心生疑问:金融城写字楼中的芸芸众生,那些饱受磨练、经历了无数次得得失失的“利己心”和“利他心”的结合体,当目光稍稍从闪动的电脑屏幕中移开,透过厚厚的玻璃幕墙,是否还会因窗外几片飘落的梧桐叶产生一丝丝特别的感觉?还会羡慕街头那十指紧扣的一脸满足?“利他心”也好,“利己心”也罢,能在金融城混都不容易,能在金融城混出个幸福生活更不容易。 金融城在金融危机中是重灾区,有人说:这年头,金融城里就是一堆堆失业的人群,没啥看头。兴衰交替是不变的规律,繁荣一定会重返金融城,怕就怕“今天很糟糕,明天更糟糕,后天会很好,但大多数人会在明天晚上消失”,希望繁荣能提前一点到来,在大多数人消失之前。
泰 晤 士 河 去看泰晤士河,是为了想像伦敦的爱情。 泰晤士河自西向东穿伦敦城而过。据说,公元初,入侵者罗马在当时潮水顺着泰晤士河所能到达的最远点建立了港口,沧海桑田,港口变成了今日的伦敦。伦敦的主要著名建筑物,包括位于地球零度东西经线上的格林威治、见证英格兰黑暗血腥时代的伦敦塔,每年夏季不断上演莎士比亚名剧的莎士比亚环形剧场、隔河相望的国会大笨钟和“伦敦眼”,宛如书画长卷展开在河的两岸,演绎着这座城市的历史。通读历史最便捷的方式是花上几英镑,坐上泰晤士河的游船走一个来回,或者再深刻点,花上几十英镑,吃顿游河晚餐,喝杯红葡萄酒,把两岸的暮色夜景看个够。 泰晤士河显著特点之一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桥,据说总共是28座。最著名的是伦敦塔桥,尽管已经很少再开开合合让大轮船通过,却依然是伦敦的象征,无论是明信片或有关英国文化的教科书,塔桥总被放在很显赫的位置。而那首脍炙人口的童谣《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伦敦大桥要垮啦)也常常误解为是描写伦敦塔桥的。事实上童谣唱的是离塔桥不远的伦敦大桥,这是一条多灾多难的大桥,多次被冲垮或毁掉,不过这条桥却有着不错的结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座百年老桥被拍卖到了的哈瓦苏湖市重新连接起来,精明的美国人当然不是意在买来一条桥,而是意在买来一个轰动效应。老桥有了好归宿,新的伦敦大桥也在原址建了起来,关于这条桥的童谣也仍在传唱,更有趣的是粤语版的居然改成了《两只雀仔跌落水》。 黄昏时分,泰晤士河上最年轻的千禧大桥是漫步的好去处。千禧大桥完工于2000年,是泰晤士河上第一座专为行人设计的桥梁。与泰晤士河上其它大桥相比,千禧大桥体型格外的苗条纤瘦,桥墩是三个轻巧的“橡皮弓”,桥身通体是铝盖板,轻盈而充满金属质感,似乎一阵风就会把桥吹动。据说,千禧大桥刚开放时,行人行走上去桥摇晃极为剧烈,结果才开放几天就被迫关闭进行结构改良,直到2002年才重新开放。千禧大桥的北端连着圣保罗大教堂,南端连着泰特现代。圣保罗大教堂是世界第二大圆顶教堂,当年在这里20岁的戴安娜披着雪白婚纱走进教堂,嫁入王室,可惜这场世人瞩目的童话式婚礼,无法带来童话式的结局。泰特现代美术馆原本是一座发电厂,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是它的标志,却被别出心裁地改造,巨大的涡轮车间被改造成了摆放艺术品的大厅,楼顶部加盖了玻璃房咖啡厅,电厂都被改成了艺术馆,伦敦当然也不再是雾都,玻璃房中游客举头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低头可以鸟瞰整个伦敦城。漫步在千禧大桥上,没有车流的干扰,远离了街道的嘈杂,微风轻拂中静静地看着两岸的城市风景,桥面把夕阳的红光泛在脸上,思想会很放松,一会飘向圣保罗教堂的穹顶,指向无穷天际,一会追随泰特馆中毕加索油画的一抹色彩,随意挥洒,一会游荡于桥下汨汨流动的泰晤士河,潮起又潮落。 在千禧大桥酝酿好情绪,接下来顺理成章要看的是滑铁卢桥, 《魂断蓝桥》中的蓝桥。滑铁卢桥始建成通车时,正值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胜拿破仑两周年,大桥由此而得名。 滑铁卢桥已不是昔日电影中的滑铁卢桥,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桥的模样却已大不一样。暮色降临,走在桥上,眼前的情景已很难跟电影中罗伊和马拉在桥上初相识的场景对接。但电影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大学上英语视听课时也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时压根没想过滑铁卢桥在哪里,更没想过要踏上大桥看看,只是在一遍又一遍的反复中记住了一个个经典的画面。因而,当倚着滑铁卢大桥围栏,身旁车光灯影掠过的时候,那些关于发生在滑铁卢桥的电影画面也在模糊中掠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一阵空袭警报传来,混乱人流中军官罗伊拉起了摔倒的芭蕾舞演员玛拉,捡起了她的象牙护身符,于是浪漫的爱情在这里开始。电影是唯美的,罗伊成熟而阳光,玛拉美丽而纯真,罗伊向玛拉的求婚匆忙而果断,温柔而炽热,两人雨中的拥吻幸福而温暖,互相拥着就是拥有了整个世界,也不知让多少看过影片无数遍的女同学在情迷意乱中悄悄把白马王子的标准抬高了。可惜,这是一部悲剧片,也是在这座桥上,以为罗伊已经阵亡、失去了爱情也失去了工作的绝望的玛拉向陌生的男人媚笑,也是这座桥上,罗伊回来了,爱情回来了,玛拉却选择了扑向迎面而来的车辆,浪漫的爱情在这里终结。夜色更浓了,泰晤士河两岸的霓虹更闪烁了。如果罗伊玛拉相识于如斯的夜晚,没有战火,没有生离死别,他们的爱情会否是另一番结局?可能会是大团圆,也可能,因为没有战火的催促,爱慕的表达或求婚都没来得那么果断,因为没有战争的分离,在一起拥吻的幸福感觉不来得那么强烈。或者可能就根本无法可能,正如《魂断蓝桥》在这个年代无法参与评奖、甚至可能无法卖座一样,时代变了,价值追求变了,技术手段变了,结果自然就变了,无论影评或爱情。 滑铁卢桥的南端是滑铁卢车站, 玛拉当年送别罗伊的站,现在是欧洲之星火车的起点站。每天,不知有多少的爱情从这里出发,穿越英吉利海峡, 开往巴黎,开往欧洲大陆,开往浪漫甜蜜。 起风了,该回去了。走进滑铁卢地铁站,踏上穿越泰晤士河的地铁,关于爱情的想像也一同上路飘荡,伴随着滑铁卢地铁站入口刻着的诗句:i dream of a green garden, where the sun feathers my face, like y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