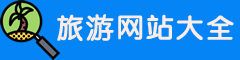|
梵蒂冈 追忆一段惨痛的历史 说起梵蒂冈,我总是感慨颇多,常常会追念那些在苦难的“文革”年代依然能不畏强暴坚持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徒们。如今,他们中许多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可他们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我,引导我认识基督普世之爱的力量,启迪我生命的真理和道路。今天,我走访梵蒂冈,带着朝敬的心,追忆那段惨痛的历史,缅怀我们中国人的“良心”。 圣地之游 梵蒂冈,可谓当今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它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呈三角形的高地上,地处台伯河右岸,以四周城墙为国界。简言之,城是梵蒂冈的首都,亦即国家,故曰“城国”。全国由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宫、博物馆、公园及几条街道组成。国中宫院、教堂、图书馆、邮局、电台、火车站、飞机场等设施一应俱全,居民多信奉天主教。梵蒂冈尽管很小,却也是欧洲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联合国派有代表,具有一个国家的地位。它是历史上教皇国的延续,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梵蒂冈城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文化瑰宝。 天主教在中世纪统治欧洲时的威严气势在此仍然得到承继。时至今日,宗教虽然退出了欧洲的政治领域,但它在欧洲人乃至全世界精神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仍然显赫。我们的大巴早上八点就赶到梵蒂冈,城外等待进入的队伍已经像盘山公路一般蜿蜒了几公里。如此多的人,各国语言在头上飞来飞去。当我们被人群推进圣彼得广场时,发觉这是个椭圆形广场,广场上到处是一堆堆人群,不少人席地而坐,诵经、交谈,一些宗教团体则在分发乾粮饮料。诺大的广场被人为地分成若干区域,巴西的、西班牙的、的。我们碰到一群亚洲年迈的老太太,是从香港组团来梵蒂冈朝圣的,其中有不少华人,我们与她们一起席地而坐休息,并与她们交谈。知道她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们的生命几乎全部奉献给了自己的“在天上的父”,从此她们成了主的女儿、女仆,许多人一生未婚。守卫和巡逻在各处的梵蒂冈卫队,是从瑞士招募来的,他们戴着帆船形状的帽子,身着蓝色衣裤、白色翻领十分鲜亮。可爱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神圣或紧张感,在各国妇女的镜头下灿烂地笑着,如同明星一般,有的对着我们快乐得挤眉弄眼。 圣彼得教堂门前的台阶下,看到一块警示牌:不准吸烟,不准吃食品;男士禁穿短裤,女士禁着露脐装和超短裙。雄浑的石圆柱构成高大的门廊,廊檐下是五扇青铜大门,宽大的铜雕大门和整块的大理石柱,使教堂显得更加气势恢宏。教堂大殿的大穹顶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装饰有极美丽的青铜浮雕,殿内的雕塑、绘画和黄金制品的艺术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在这儿,里里外外游人如织。其中既有如我辈的普通旅游者,也有虔诚的教徒。肃穆幽微而又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内,闲散的拍照者和祈祷的朝观者两不相扰。在大教堂里,可以看到教皇登基的圣台,以及无数雕刻或绘制精美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站在其下,顿觉自身的渺小。而门的名称更让人心生畏惧,中间那扇叫善门,左边两扇叫神门和死门,右边两扇是圣门和灾门。我们是从善门进去,由灾门出来的。圣门一般不开,每隔二十五年的圣诞之夜才开一次,由教皇亲自来开启。但有重大圣事活动时也可以打破常规。步入教堂,首先来到大厅中央。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高远的大穹顶下,是青铜华盖,华盖之下是教皇举行弥撒的祭坛。在祭坛两旁,各有一架大管风琴。举行弥撒时,管风琴里奏出的低沉、舒缓的旋律回旋在整个大厅。祭坛前面不远处有一条通道直通教堂的地下室,地下室在十六世纪时扩建成一所巨大的墓室,之后的历代教皇都安葬在此。 圣彼得大教堂四周建有不少各具特色的礼拜堂,而每一座礼拜堂都是一个小小的艺术馆,里面布满了历史上著名艺术大师的作品。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圣母悲切礼拜堂,因为这里面收藏着米开朗基罗雕塑的成名作《悲切》。圣母眼帘低垂,无限哀伤地看着怀中的耶稣。在这块弹丸之地上聚集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一大批举世无双的艺术财富,完好的保存并展示在世人面前。 梵蒂冈的日常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每遇周日,圣伯多禄广场天主教徒聚集,中午12点,随着教堂钟声响起,教皇在圣伯多禄大教堂楼顶正中窗口出现,向教徒们发表演说。导游带我们参观了有五百年历史的圣伯多禄大殿,这是每年主持国际圣体大会和圣体年揭幕弥撒大典的场所。大殿堂是基督教的中心,站在这座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的大殿上,我想起一个曾经在市监狱相遇的难友。我大胆问导游:听说1991年在这所大殿中为原上海主教龚品梅举行过欢迎与加冕仪式?他惊讶问: 地狱之忆 参观梵蒂冈触动我想起解放后中国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悲惨命运。1966年当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噩运就降临到远东著名的天主教上海教区,其中心即在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院、神学院、天文台等方圆几公里地方。解放前上海教区管辖面积据说超过梵蒂冈国土,在上海地方史料上,这里曾有“东方梵蒂冈”之称。著名的徐家汇藏书楼,原是教会图书馆和耶稣会综合研究机构,中国第一本外文百科全书就在这里诞生。旁边有百年历史的徐汇中学,原是徐汇公学。现在徐汇区政府的办公大楼与上海天文台,则是原天主教大修院、神学院、拯救女修会和献堂会。附近的土山湾地区是教会各种用品、服装的生产基地,中国最早的西洋油画作坊就诞生在这里。在大教堂后面的汇南街还有中国最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陵墓,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的噩运随着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一声礼炮,在这里拉开前幕。 第一次大规模游街是8月3日,北京与上海红卫兵冲进大教堂,把神父修女们床上用来压蚊帐的二米长的棍棒抽出来,人手一根,像对牲畜一样抽打驱赶出全部神职人员。红卫兵给他们每人头戴二公尺高的牛鬼帽,领头的是爱国会主教张家树和李光明神父,高帽不够红卫兵就用花盆、痰盂扣在他们头上,用长绳索牵连着,“牛鬼蛇神”大游斗开始。红卫兵强迫他们呼喊“打倒天主!毛主席万岁!”沿着徐家汇路步行到路,再到路,原路再折回来。一路上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在红卫兵喇叭的煽动下,愚昧无知的革命群众、大人小孩用石头、垃圾、脏水、烂菜皮扔向他们,肆意凌辱这些天主的使者。近三个小时的游斗,年老走不动的神父修女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互相搀扶着起来,而红卫兵的棍子皮带不断毫不留情落地在那些不肯喊“打倒天主”的神父修女的头上身上。要知道被游斗的这些人都是在爱国会领导下宗教团体的教徒,他们都妥协过——“爱天主、也爱毛泽东”。但今天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叛离天主、只能爱毛泽东”。几天后,第二次大规模游街又发生了,如法炮制一直游街到徐家汇的徐光启陵墓小公园。红卫兵对着当地教徒的面,把他们敬重的天主教徒科学家的墓彻底毁坏,并扬尸在外。 我对上帝基督耶稣的认识有四十年之久,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文革前我因出身不好与腿残被拒之于大学校门外,进了一家200人街道小厂,它位于徐家汇天主大教堂后面汇南街上,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厂里职工信天主教很多。文革一开始厂里教徒们就被剥夺了上教堂做礼拜的权利,而且要向工作组交出圣经与互相检举揭发教友的言行,并写下脱离教会的保证。一些顽固内教人均遭批斗抄家,个别忠诚信徒遭迫害后自杀。我不仅看到了厂里教徒的迫害情况,更是目睹了近工厂百米的徐家汇天主教堂的一场劫难。1966年我才十九岁,这一幕幕残酷的社会与家庭冲击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恨文革、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这批人。十月因参于三哥反对攻击文化大革命一案,遭逮捕入狱。我在“一所”曾待了四年,那里是关押上海重要反革命政治犯重地,在里面我相遇了许多基督神职人员,与他们长期的难友生活使我真正接触到基督教义与精神,开始对“上帝、耶稣、圣经”有所了解。我知道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来到世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也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蒙恩成为神儿女的道理。这些神职难友还告诉我:经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跟随主走苦路是必经之路,靠主克服自己肉体的软弱”。他们教我如何向主祷告,如何把自己完全交托主,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他们一直卑微地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即使身陷囹圄,却始终至死不渝地持守着自己的信仰,在监狱里时刻不忘向难友传讲天国的福音。因着他们的带领,我开始信主了。 记得其中有四个人给了我很深教诲与基督的启蒙。第一位是毕业于震旦大学的张宏根神父,他告诉我: 第二位是耶稣会的胡永康神父。1951年10月8日,政府宣称“圣母军”是反动组织,一夜间所有教会学校开始肃清抓捕参加圣母军的青年学子。当时他在震旦附中读初中(14岁),因为信仰,这群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了爱尔兰籍莫克勒神父倡导的保卫圣母的“慈母圣教会”(圣母军)。“当时公安追、学校赶、父母哭,四面楚歌,工作组逼父母,叫我们登记承认参加‘圣母军’,并写诲过书。我年幼被母亲领回家,但同样没逃过58年的又一次反梵蒂冈划界线运动。他在一所关很长时间。我在一所与他相识,胡神父曾劝导我,“神给了每个人宝贵的时间,你不要浪费它,有时间就有机会,你只有十九岁就像块海绵一样,利用这特殊环境能接触到你一生中都不容易碰到的人,努力学知识、吸收营养,将来你会感到幸尝智慧果。” 他告诉我:自己不能事奉两个主人,毛泽东和上帝,不然良心将终日不安,即使释放了,也要变成疯子。他还说:自己是“因信守义、才有了属灵的生命”。 还有二位都是徐家汇天主教堂神职人员,一位是大名鼎鼎龚品梅主教,另一位是默默无闻的盲人修士金林生。回忆这二人的劫难就更能清楚了解解放后中国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悲惨命运。1951年中国第一次反梵蒂冈运动,历时一年半,起因是梵蒂冈驻中国公使黎培理被驱逐出境一事;1953年中国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驱赶所有在中国的外国籍传教士;1955年9月8日是天主教的大灾难日,宗教界称为“九·八事件”。政府一夜间在全国逮捕了所有抵制,共产党领导“三自革新”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人士。在上海,龚品梅、金鲁贤等百多名神父和上千名教徒被捕,后来漫延到全国各地教会,许多人被判二十年或无期徒刑。1958年又一次反梵蒂冈运动开始,政府利用宗教界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在天主教内部造反分化,这是一次重要的划清界线运动。凡爱国者,跟共产党走;爱上帝者,软禁起来,有影响的则被抓进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彻底取缔了天主教与基督等其它宗教团体活动。 盲修士 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们嫌光游街还不够剌激,又组织了大规模批斗会,并强迫当地天主教信徒去观看接受教育,我厂天主教徒也被迫去观慕。近五十名神父修女被押到徐汇大教堂广场前,列队被批斗,红卫兵逼他们把《圣经》“十字架”踩在脚底下,每人手拿红卫兵硬发给他们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天主!”“打倒圣母玛利亚!”、“打倒圣子耶稣!”,并要三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小时折磨下来,个别人违心而痛苦地呼喊了打倒自己心中的主——“天主”。于是,红卫兵允许他们脱离批斗,绝大多数不肯高呼“打倒天主”的人则被“加温”,各人脖子挂上十几斤重的木牌子,再不屈服,红卫兵上前两个挟一地强逼他们弯腰九十度,接着干脆把他们双手反背,做“喷气式”飞机状,甚至逼令他们跪下,疯狂地对他们拳打脚踢。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一致高喊“打倒天主!”“打倒帝国主义!”“神父修士是反革命坏蛋!”“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在如此人格侮辱、尊严践踏、肉体摧残下,不少年迈体弱的神父修女纷纷昏倒被拖走。红卫兵用尽了一切手段,几个小时的折磨中,有一位双目失明的修士始终紧闭着嘴巴,死死不吭一声。红卫兵敲开他的嘴巴敲掉他牙齿,硬逼他呼叫“打倒天主”,从他嘴里吐出了鲜血与打碎的牙齿,谁知最后,他拼着命喊出了一声谁也料想不到的口号“蒋XX万岁!”这使横扫长城内外、斗遍大江南北、战无不胜的北京红卫兵气疯了,竟然遇到了一个不怕死打不败的天主教牛鬼人物!末了,红卫兵得出结论:这个帝国主义驯养出来的宗教走狗,一定是个隐藏很久的美蒋特务、梵蒂冈间谍。于是北京红卫兵们收场时把他押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罪名是他批斗时竟敢呼喊人民公敌蒋某万岁,而他那用手摸写的密密麻麻的盲文外文字母肯定是间谍收集的情报。 盲修士叫金林生,出身在上海浦东地区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少年到青年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来从公教青年教徒变成终生为教会服务的修士(不结婚),一直在上海市徐家汇天主教堂任职。29岁时的一场大病不幸使他双目失明,失明后的他主要任职宗教文献的盲文翻译工作。因为他双目失明长期不外出,经常独自一个人关在阁楼上,又是一般低级神职修士,所以几次打击宗教运动都能逃脱。然而文化大革命对宗教进行全面迫害,一个不放过,红卫兵造反派叫他学习,被他拒绝,捆绑硬拖进学习班,他仍拒绝学习毛选,只读经书;遭批斗殴打,他不为所动,还是只认天主,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甚至于他还几次主动要求进监狱,工作组造反派对他也很无奈。金修士认为所有兄弟姐妹都进过监狱,唯有他自己没能享受这种荣耀不甘心。当时许多奉献天主的神职人员,都拿耶稣作为榜样,私下准备好把监狱作为一生磨难的终结地。他们以苦为乐,把监狱当考验自己的意志、考验自己对上帝忠诚程度的磨难处。他们认为活着是临时的,而死才是永生,都甘愿杀身成仁让灵魂进天堂。金修士的盲文外文数据经公安局技术鉴定,全非特务密码,更非间谍情报,纯属宗教内容,所以专业有识人士对红卫兵的无稽之谈也只得苦笑不已。审讯他的人员多次问他为什么要喊人民公敌蒋某万岁?是否不想活了?他回答说:“我想进监狱。”又说:“蒋宋都是基督徒,今天如果他们在中国,绝不会允许这种迫害宗教人士,丧尽天良的事发生。” 冬天来了,金修士只穿一套单薄的修士服。那些良心泯灭的看守有意要折磨他冻他,以便让他屈服开口求饶,只发给他一套囚犯穿坏的破棉衣裤、一条薄棉被。在零下的冰冻寒天,他瑟瑟发抖,冻得脸皮发青,手脚冰冷。他每天咳得很厉害,多次发高烧吐血被送市监医院抢救,从医生处我们知道他在外面就有严重肺病。监狱负责看管人员要他写下放弃信仰天主的保证书,哪怕口头说一句,表示向无产阶级专政投降,马上可以宽容照顾他,通知外面送药品或吃病号饭。更令人气愤的是,外面教会邮寄给他的衣服、棉被,被一直扣押到第二年四月春暖花开时才给他。我们从包裹单上清楚的看出,邮包寄出的日期是去年11月份。同时我们听看守说,因为他不放弃天主,外面送来的营养补品都不能给他。偏偏这个“不识抬举”的修士宁愿关在里面也休想从他嘴里吐出一句不敬天主的话。他每天依然正襟打坐,嘴里念着经文,从不向看守开口求饶。 最使我们对金修士惊讶不已的还有一件事。所里犯人每星期五是开荤日,这一顿荤菜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珍贵了,因为哪怕你有再多的钱,做了囚犯是买不到这宝贵的一小块肉的,更别谈从最低营养角度说这小块肉以及有限的肉汤对犯人有多重要。因此,每个人都渴望一周中的星期五。可巧天主教规定星期五是守小斋的日子。实际上,盲人修士也可以申请吃回教饭。看守和训导员都说过,只要他开口批判一声耶稣天主,马上照顾他,可是他断然拒绝了。就这样,金修士从进监牢至今二年多没有沾到一点荤食,这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盲人修士体内得不到脂肪、蛋白质补充,加上肺病自然骨瘦如柴。他靠的是什么样的毅力支撑?当时我们简直无法理解。他曾说,他在学耶稣受难。众所周知,耶稣被四肢钉在十字架,不久活活被折磨死了。这位盲人修士二年多来精神上肉体上遭受严酷的折磨,不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正直良心的人谁见了都会伤心落泪。当时我惊疑:关在里面都是政治犯,算得上有思想有意志,可还是一般的“肉身”,我们在监狱怕饥饿、怕恐惧、怕孤独,唯独他的肉身是“道”的载体,什么都不怕。仿佛基督的精神灵魂熔化附着在他的“肉身”上,充满钉死十字架无所畏惧的勇气。 我对金修士讲了古代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劝他认错,好汉不吃眼前亏,来日方长。金修士却摇摇头,认为那是对天主的亵渎,比死的罪孽还深。他说,“我为什么要说不合天主神旨意的胡话?现在是假神取代了真神,我不能做叛徒犹大。我要保持信仰的纯洁,不要为了活命、为了求生而糟蹋自己的人格。这是不值得的。其实死与生是一回事,天主是知道的,会安排一切。”金修士还告诉我:他要学二个兄弟神父张忠明、候之桢的榜样,关死在监狱也不背叛主耶稣。他常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跟主走苦路,是主给我的恩宠。”他教我祷告、托付主、跟从主,说这样能克服自己的软弱。他告诉我:“眼虽瞎了,但主让他看到了光”。 每逢星期五囚犯开荤日,他绝食抗议,通过惩罚己身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内心除了虔诚笃信天主教之外,毫无其它杂念。他对同监犯人的讽刺嘲笑,对看守的凌辱和别人对天主极其不恭的言行,或在别人谈论文革种种暴虐时,反而怀有一种极强烈的负罪感。他从不责备别人,把监牢里所有的犯人当自己兄弟。他常常为那些文革中被利用过后,也关押进一所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的深重罪孽而痛苦不安,为摆脱他们的罪孽,为他们忏悔、祈祷。有次我问他:“文革”如此罪孽,究竟有无使中国人灵魂得到解放之途径呢?“文革”使中华天地浑浊,人们痛不欲生,芸芸众生,劫难茫茫,如何生活得下去?盲人修士冥思了半天,默默念诵《圣经》,然后说道:“《圣经》记载,天主之义是本于‘信’。‘义’为灵魂得救之意,‘信’乃得救之路。‘信’者,信仰也。我国文明始祖孔子也说过:‘民无信不立。’一个人失去了正确的信仰,一个民族失去了正义信仰,必然被邪恶所愚弄、所蹂躏。”金修士告诉我:天主爱全世界的人,如同爱一个人一样,我们应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像耶稣一样使人与人之间成为兄弟关系。 金修士是我接受基督的启 金修士因为肺病长期缺乏营养药品,多次发病吐血去医院抢救,他的审讯员不希望他死在监狱,有意想放他出去保外就医,唯一条件就是让他认罪,放弃天主。当时哪一个囚犯都不会放弃“写张认罪书先逃出地狱再说”的机会,但我们看到,所有的诱惑都一再被得重病的金修士大义凛然拒绝。 记得一次,牢房内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头头想立功,向训导员揭发金修士顽固不化,每天吃饭前坚持祈祷,并说:“圣经是他的生命粮食,祈祷犹如呼吸”。训导员把我们全体叫去训话,痛骂修士不思悔改,叫我们不要受他拒绝改造的影响。训导员再一次引诱他,打开一只寄给他的邮包,里面除了衣服日用品,还有一本盲文圣经与进口营养品。训导员要他认错,保证不在牢房祈祷,这些东西可以拿去。修士摇头表示拒绝,但他要求政府能留给他这本盲文圣经。怒气冲天的队长说:你把圣经当粮食,今天就给你挑选,要圣经的话,从明天开始停止供应吃饭,看你能坚持几天?金修士毫不犹豫伸出手,要圣经当粮食。队长气疯了,边撕圣经抛在他脸上,边狂骂道:“邪教,去你妈的上帝”!金修士颤抖着双手,拼命摸索着地上被撕毁的圣经,流下了乾枯的眼泪。这是我二年中第一次看他掉眼泪。 为了严惩修士的所谓反革命言论:“神的话是他生命的粮”。训导员给他上了铐,并决定不给他饭吃,看他能坚持几天来讨饶。顽强的修士宁饿死不求饶,身体虚弱的他第三天昏迷倒下,政府无奈只得送他去提蓝桥监狱医院抢救。同监难友们被他纯净而正义的灵魂所震撼,私下都称他为“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活耶稣”。 老主教 后来我被判反革命罪,到市监狱一中队服刑时,又相遇到老主教龚品梅。我小时曾从父亲嘴里知道,龚品梅19岁进神学院、29岁当神父,长期任著名教会学校震旦附中的校长,在上海是个有名望令人尊敬的主教。而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三哥告诉我,当时天主教里有句话“全国看上海,上海看震旦”。震旦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前身)曾培养出无数基督精英,可惜大多数人遭劫难。1950年,梵蒂冈任命龚品梅为上海南京苏州三地主教。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一个尖锐激化的矛盾,共产党组织了新的爱国教会,要龚品梅脱离梵蒂冈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三自革新”会,可是不识相的主教抵制政府对天主教的改造和渗透,要求独立,拒绝在教会内开展反帝(梵蒂冈)爱国运动,拒不参加官方的爱国组织,于是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 那时我关在市监狱大刑犯一中队的老残病弱四楼,做一些“拆纱头”的轻微劳动,我在第三小组,第四组最后一间牢房就单独关着所有犯人都知道的特殊人物,上海天主教主教龚品梅。他属于比较特殊照顾的犯人,当时楼面上还关了不少判重刑年迈的宗教名人,如跟我同组的上海教区谘议员德肋撤堂的本堂张希斌神父,他曾是杨州震旦中学校长。龚品梅他们从1955年失去自由,在一所关押五年,后判无期徒刑进市监狱,曾押送到外地劳改场改造过,在失去劳动力后又押回到上海市监狱大刑犯一中队关押。71年监狱鼓励互相告密立功减刑,政府得到举报,这些判重刑的神父、牧师,长期坚持每天早晚做祈祷,甚至在监狱继续暗中传教、传播福音与圣经,抵止洗脑、不认真背诵毛选,却天天默背圣经。政府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大逆不道反动的,是一种蔑视专政机关的挑战,一定要组织犯人肃清流毒彻底批斗。为此,在犯人中组织了一次气势较大为期九个月的“破有神论学习”运动。当时管教队长布置楼面多次批斗帮促龚品梅他们。 我至今难忘学习班结束的这一幕,七十多岁的主教弯腰低着头,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听凭犯人对他“反动思想”的批判。我为他庆幸的是一中队的批斗会比较文雅,因为参加者大多数是政治犯、长刑犯、老年人,加上中队长叮嘱此人特殊不要动手,主教免除了皮肉之苦。如果换在我曾经历过的其它中队,特别是刑事犯中队,主教的老命危险矣!几个月的批斗“帮助”对他无动于衷,他几乎成了哑巴,一句不答。结束会这天管教大队长问他: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帮促你觉悟了没有?现在“你对天主信仰怎么认识?”主教用心平气和的语调回答:“宗教信仰不变”。队长气怒地骂道:“你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反革命,如果天国中真有上帝,你也就不会在这里了。”这时,我发觉主教第一次抬起头看着我们,那眼神充满了悲忧,却又那么慈祥,就像耶稣被捕后被门徒彼得否认三次,望着彼得时的眼神一样。随后队长凶狠地说:“还有谁坚持信基督的,有种都站出来?”张希斌神父第一个站出来,接着先后五位陪帮促神父牧师都站出来。管教干部歇斯底里大发作,狂叫:“好!你们等着瞧!将来有得加刑,有得要处死你们这些邪教”。气疯的队长叫来几个犯人打手,用木板猛击张神父他们倒地为止。记得当时有个姓沈的神父倒下前还说了一句:“我们没有反对政府,是共产党要置天主教于死地”。当时我们参加批斗会的犯人心里既震撼又难过,这一幕永远留在我人生脑海中。显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这批耶稣会神职人员起不到作用,他们“生是基督、死是福”的精神,击败了政府组织的这场所谓“破有神论学习运动”。 记得一次在楼面放风时,我趁旁边无人悄悄走在龚主教旁问,是否知道徐家汇天主教堂的盲人金修士?他惊奇地问我:是否双目失明的金林生修士?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知道金兄弟。我告诉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与金修士共同生活了二年的情况,及金修士愈来愈差的病躯,并说了政府工作人员当我们面讲的话“只要金表态放弃信仰天主,马上保外释放他”。龚主教坚定地回答:“休想!金兄弟宁肯死,也不会讲一句背叛天主的话。”后来我知道,这也是龚主教坐三十三年牢狱的誓言。 十三年牢狱之灾中我相遇到不少意志坚强、宁死不屈的政治犯,而最使我敬佩的就是那些天主教、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神学院毕业的耶稣会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他们身上都有基督教义所倡导的美德:谦卑、温柔、忍耐,而几乎所有这类人都是“道”成肉身,准备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年轻时始终搞不清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在地狱中不屈不挠,他们躯体内注入的“道”是什么东西,具有这么样强的受难精神?后来,当我接触到更多的基督教政治犯,及读到《圣经》后才明白是天主的教诲、是耶稣的榜样、是基督的精神支撑着他们。我后来才知道,解放后毛泽东对他们的打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并越演越烈。职业教士多数人长期在漫长的监狱和社会的管制监督中接受强迫洗脑,但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我在黑暗地狱中行走了十三年,每次无望绝望感觉持撑不下去的时候,总是基督神职人员的榜样和言行告诉我:“耶稣是世界的光,跟随它会走出黑暗。 我平反出狱后,去徐家汇天主教堂探听一些在监狱相识的宗教人士,我碰到了前后关押二十多年活着出来的张神父,得知金修士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关了六年,最后死在监狱里。而龚品梅被关了三十多年,1985年在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宣布龚品梅承认错误被假释。令人想不到的是,当时八十多岁的龚品梅拒绝出狱,拒绝在所谓“改造好提前释放”的证明上签字。最后,政府把他放回徐家汇天主大教堂交爱国会看管。1987年,他因心脏病被批准去医治。1991年梵蒂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伯多禄大堂用最高规格接待和欢迎他,并封他为枢机主教(即红衣主教,是教皇下的最高职称),许多西方首脑和天主与基督宗教教袖出席盛会,全体长时期起立向他致敬。实际上,早在1979年龚品梅还在狱中时梵蒂冈就已秘密任命他为枢机主教,梵蒂冈的这一举动在外交上与中国深深结怨至今。2000年,98岁的龚品梅得胃癌在美国去世,迄今在基督世界享有盛名。我想南非曼德位为信仰坐了二十多年牢,出狱后被非洲黑人当伟人、民族英雄。龚主教同样为了信仰坐了三十多年牢,他几乎都是一人独囚一室,就这一点,他比任何人受的苦多深,他没有被逼得精神失常或患严重忧郁症,是上帝的恩赐。今天基督世界给了他崇高荣耀,封他为教会亲王。但中国给了他什么?难道历史就不能还他一个公道吗? 我一直在思考:毛泽东为什么对宗教这么仇恨?特别是对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恨与怕甚至远超过佛教和传统的儒家?关键就是一本书——“圣经”与“毛选”,一个人——“上帝”与“毛泽东”;其核心就是“圣经、上帝、耶稣、所传播的基督普世价值观。文革时毛泽东把宗教诬批为人民的鸦片,他让红卫兵大量焚烧《圣经》等宗教书籍时,又强制老百姓人人拿一本红宝书,还叫亿万人民把他当神供起来。但他的红宝书能与《圣经》相比吗?毛泽东思想能与普世主义相比吗?和今天大批涌向教堂做礼拜读《圣经》的芸芸教徒相比,现在还有谁手捧着红宝书呢?和世界各国都在推行普世主义相比,还有那个国家在高举毛泽东思想呢?在我十三年监狱里接触到的天主教基督教徒们中,他们很少有一句“反党言行”,说白了,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只听天主、不听毛泽东”;他们的反革命罪状就是向教徒“只宣传圣经中普世价值、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在毛时代是大逆不道,是没有活路的!他们一直卑微地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我却认为他们是道德的化身。十三年中我在监狱与劳改农场极少见到过信仰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刑事犯。想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平反的冤假错案数量还少吗?公布出来的材料还不够荒唐吗?连新中国的奠造功臣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可以随便被诬陷连扣五顶“反革命帽子”而致于死地,拿一个梵蒂冈的使者开刀,判他无期徒刑当然更无所谓。判龚品梅无期徒刑,目的就是警告中国所有信仰基督的人——中国大陆不允许有“天主”,只有大救星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梵蒂冈一直没有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打击外交,直到现在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二十来个国家,差不多都是受梵蒂冈的宗教影响与支持,这也是新中国与梵蒂冈关系恶交不能恢复正常邦交的原因之一,当然也与龚品梅、盲修士这些无数的天主教徒当年在大陆遭遇的命运有关。 回顾这段惨痛的历史,我想不明白:难道宗教在中国真有这么可恨,非要置于死地?联想到如今的中国,我常常会想起托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什么都可以干。”是的,无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愚昧、残忍、丧尽天良的浩劫,还是如今社会上的犬儒主义、拜金主义,都是与我们国人缺少信仰有着紧密的关系。有了信仰的人,精神有了依靠、灵魂得到安抚。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还是传统的儒家文化,都要求人们向善避恶、相爱相助。它们对老百姓来说,既是信仰,也是一种社会道德的修养课,这样的信仰有过错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改革开放后,富裕了却依旧迷茫困惑的人们更加渴望精神上的引导和依靠,基督教、佛教而今又在迅速扩展。过去与今天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