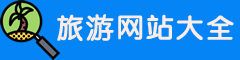|
“特色小镇”这一术语正式出现于2015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本意,“特色小镇”原拟用作经济新常态时期产、城、人、文融合的重要平台,力促产业、旅游、文化和社区功能的协力发展,以更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建设一个富且美的浙江。 随着2016年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发布,例如,《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建村[2016]147号)和《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6]2125号),“特色小镇”建设在国内渐趋遍地开花之态势。 即便在浙江,特色小镇也存在相应问题,距离“以人为本”准则的落实,尚任重道远。 例如,小镇的内涵和“名号”何以对接?从浙江已经公布的78个创建名单去看(原为79个,后来“奉化滨海养生小镇”被降格,事因投资方宝能集团与万科之间股权争夺),五花八门、与本土历史文化或产业基础基本不搭边的命名方式纷纷“横空出世”,比如“巧克力甜蜜小镇”、“云制造小镇”、“时尚制造小镇”、“硅谷小镇”、“光伏小镇”、“核电小镇”等。还有一些小镇的名字也很奇怪,例如“模客小镇”、“生命健康小镇”、“健康食品小镇”、“天使小镇”、“(森林、神仙)氧吧小镇”等。 其中,“云技术、财富、金融、高科技”等成为热门高频词,似乎成了高端新兴产业的代名词。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共通之处,可能就是为了吸引投资,这是因为,截至目前,投资的额度和进度是特色小镇建设考核的关键性指标构成。 丰满的理想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特色小镇一要有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二要有和谐宜居的美丽环境,三要能够彰显特色的传统文化,四要有便捷完善的设施服务,五要有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住建部村镇司司长张学勤也曾表示(2016),特色小镇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要逐渐形成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间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格局,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围绕人的城镇化,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功能,补齐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短板,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防止形象工程”。 与此同时,特色小镇建设,着力点在于以地域性“特色文化”和“特色产业”以及二者融合,作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新时期突破口。为此,特色小镇建设需要有益于能够有机对接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其中,“特色产业还应该具有产业带动作用以及较好的产业发展创新环境。产业带动作用分农村劳动力带动、农业带动、农民收入带动等三个方面,分别用农村就业人口占本镇就业总人口比例、城乡居民收入比等定量数据表征”(《国家特色小镇认定标准》)。 骨感的现实浙江特色小镇的创建,从一开始至今,就始终坚持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也即主要遵循“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原则,“主要目的是在新常态下助推产业转型,对特色产业投资的要求不会降低”。事实上,浙江省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提出,浙江未来重点打造的是信息、金融、健康、旅游、环保、时尚、高端装备制造和文化等“八大万亿产业”。 实际上,存在两种版本的特色小镇,即政府版“特色小镇”与市场版“特色小镇”。前者主要以政府规划为主,后者主要是地产开发商在操办,比如,万科的“良渚模式”(杭州万科良渚文化村),另一个地产大亨蓝城集团则选择了以“农业为主题”的小镇建设作为集团主打业务,如绍兴嵊州的“农庄小镇”。这些开发商项目都极具诱惑力,尤其是善于捕捉“品味人士的心思”,以“美丽建筑”打造“美好生活”,建筑“新都市主义人居场所”。 2017年6月20日,住建部原副部长刘志峰在由新京报主办的“遇见中国特色小镇启动峰会”上表示,自2016年三部委联合发文后(建村[2016]147号),特色小镇建设已经出现生搬硬套、同质化严重等问题,“特色小镇需要降温”了。 而且,尽管官方文件规定,鼓励社会组织和市民成为小镇建设的主力军之一,但从多地实践去观察,社会的力量在哪里,目前尚不明朗,服务于“创新社会治理”目标的声音最为渺小。 于是,关于特色小镇建设,或许需要进一步探讨:缺失投资和产业集聚、常住人口和稳定就业率的特色小镇,建成之后如何可持续?这样的特色小镇是否终将沦落为一些广为诟病的房地产开发或者产业园项目(如“圈地+圈钱”)? “丰满理想”和“骨感现实”如何相衔接借鉴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地方振兴方面的一些经验,如“总体营造”和“地域活化运动”等,关于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丰满理想”和“骨感现实”如何相衔接,或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对“人”及其参与性的重视不足 从截至目前的一些实践运作情形去观察,特色小镇建设对于“产业”非常重视,但对于“人”的位置这一点,尤其是在地居民权益维护和保障方面,在官方版“特色小镇”实施意见中,依然较为模棱两可。须知,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地方民意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合作是影响小镇未来的一个重要变项。 关于“特色小镇”主体,官方说法有:企业为主模式(如山南基金小镇);政府和企业相结合双主体模式(如云栖小镇)。而“特色小镇”管理者目前依然是传统的开发区管委会。参照台湾经验,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需要厘清几个关键问题,即它们是谁的“小镇”,谁是“小镇”长期建设的主体,比如,是产业资本者,政府项目打造者,抑或是包括在地居民在内全体使用者。再如,建设主体如何行使建设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以及“小镇”建设资源分配以什么为基准点进行配置和协调,等等。 既有官方话语体系中,特色小镇建设的目标在于,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与新一轮“产、城(镇)、人”三者融合的重要平台。但是,不论是从文件内容本身,还是从现有实践讯息反馈去观察,更多的好像依然是在讨论产业集聚,或者产城(镇)融合。至于“人”如何与此二者融合,则语焉不详。比如,即便有所论述,也只是泛泛提及“人才”,而非小镇建设区块上的“在地居民”。导致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部分“特色小镇”为“征地”后的新造产物(如名声在外的杭州“梦想小镇”),因此,官方眼中暂时可能只有“引进人才”,而无在地居民。 并且,在小镇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过往开发区、产业园建设旧式样,尚未见到“地方社区的主体精神”及其功能发挥。例如,镇区在地居民参与未受到应有重视,遑论在地居民如何融入小镇建设中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等切身利益需求了;镇区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培塑方面被忽视,以及在小镇特色界定和自身资源深度发掘方面,政府主导印记过于明显,等等。 概而言之,截至目前,在“特色小镇”选取和建设过程中,在地居民并未被有效“赋权”,也欠缺参与“小镇”建设的有效渠道。而“厚植人力”才有助于地域活力永续发展的实现。 (二)地方经济重建的动力在于地方社会的重构 承上,倘若纵观台湾和日本的地域活化实践,不难发现,大致均体现为,一个地域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后都走入了一个经济放缓阶段,都面对着重重社会问题,都是对经济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如何能够更加和谐有序发展的社会性反思与结晶。实际上,浙江推出“特色小镇”的背景与此有着类似相关性,即助推新常态下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寻求新际遇与相应发展空间,例如,从“块状经济”历史迈入“小镇模式”未来。但是,真要实现这类转型发展诉求,在地域活化路径认识方面则有待于深化,比如,关于“地方经济重建的动力在于地方社会的重构”的社会学解读。 首先,“特色小镇”建设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建筑聚合,也不只是一个产业(聚合带)的经营,还是融含有地方社会协力治理的地域再生与活化。以首批37个小镇名单为例,其实,官方“特色小镇”名单公布仅仅只是“建设”的开始,而不是“建设”的结果。“特色小镇”建设当是一个可持续、不断发展的事业,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产业)项目,而且,此种延续性可以依据需求改变而更新变化。地域活化和再生不只是景观格局的塑造,也不只是特定产业的复苏或开拓,还要能脚踏实地为在地民众提供生活的便利与舒适,在这其中,镇区同一地域空间的社会文化再生意义并不亚于其经济再造功用价值。 其次,一定意义上,台湾在地方振兴过程中曾经浮现过“空间性和社会性隔阂”问题,也是浙江“特色小镇”建设在推进过程中最值得警惕的问题之一。参照台湾新竹科技城案例,可以知晓,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与“小镇”在地居民意愿(利益)关系如何平衡梳理,是未来“特色小镇”建设的一大挑战。这一点,对于以7大领域高科技产业类型为主“特色小镇”而言格外重要,这是因为,这种类型“特色小镇”很多是“新鲜制造”的产物。其中“外地”和“在地”之间需要磨合之处特别多。如果不能满足镇区这两类人群的真实需求(如教育、医疗、住房、休闲等),则不仅难以获得他们的支持,甚至可能在开发过程中导致对镇区原居民既有生活空间使用性的某种压迫,制造出新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