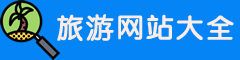|
澳洲饭店(Australian Hotel)是一个有着爱德华时代内陆风格的酒馆,咫尺之遥就是悉尼的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我坐在它的遮阳篷下,面临着极其困难的抉择。如果点了袋鼠肉,以后我还能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下去吗?记得小时候在动物园里看到袋鼠蹦蹦跳跳,极其可爱的样子,当时就对爸爸妈妈说长大后一定要养一只当宠物,而如今他们却“躺”在我的餐桌上,可谓是另一番“亲密接触” 。
独一无二的天际线:一望即知的歌剧院和港口轮渡,在华灯初上和最后一抹残阳的映照下,显得愈加美丽。 抵达悉尼才两天,我那喜欢美食的朋友就对我“投下一枚炸弹”。她告诉我说,澳大利亚人其实是吃袋鼠肉的。他们还吃鸸鹋、木蠹蛾幼虫和鳄鱼。产自内陆的食物被称为“丛林美味”,袋鼠肉排,尤其是瘦肉排,用罗望子腌了后烤起来吃,味道好极了。我到澳洲饭店是因为这里擅做各种“丛林美味”;但如果午餐吃了“跳跳”,我以后可能就再也无法面对镜子中的自己了。我想起这次穿越太平洋的使命——寻找能够定义悉尼的味道,那是文化和环境完美结合的一刻,你会发现究竟是什么让你打那么老远来到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这种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在面对一盘不甚了了却可口的美食时。我很清楚,当悉尼的味道到来时,我一定会马上识别出来。但最好不要是袋鼠肉。这么说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刚在悉尼的塔朗加动物园(Taronga Zoo)待了一个下午,在那里看到了极其机敏的澳大利亚野狗、大洋洲特有的鸭嘴兽,以及长着圆脸蛋的考拉。最令我难忘的,是与沙袋鼠、小袋鼠和鸸鹋一起度过的那半个时辰的快乐时光——塔朗加动物园允许游客在一片围起来的地方自由游荡。袋鼠跳来跳去,用鼻子轻抚育儿袋里的小袋鼠,或懒洋洋地站在树荫处。它们看起来生就充满母爱,极其慈祥,而且绝不像是可以吃的样子。 码头餐厅(Pier)可口的旭蟹和头盘扇贝酸橘汁腌鱼值得一试 于是,当听到坐在隔壁桌子的一家人犹豫究竟是吃袋鼠还是鸸鹋的时候,我决定采取折中的做法。忘掉跳跳吧,我决定了,就点盐水鳄鱼。在塔朗加动物园的时候,我看见这种畜牲潜伏在池塘里,只有鼻子稍稍露出水面。它们可以长到6米长,在过去的35年里,澳大利亚至少有60个人遭到鳄鱼的袭击。吃一顿鳄鱼大餐,算是它们应得的报应。服务生端上来的鳄鱼肉放在一小块比萨上,坚硬的鳄鱼皮换成了椰浆,上面还覆盖着泰式药草以及四分之一片的酸橙。肉切得很细,卷曲的肉边稍稍有点烤焦了,看上去就像是一坨融化的莫泽雷勒干酪。 至于说到鳄鱼肉的味道——嗯,当我迫于实情以及所做过的“不能撒谎”的许诺,而写下“鳄鱼肉吃起来跟鸡肉没什么两样”时,我可以断言自己不可能在悉尼 找到山珍海味了。 “丛林美味?”巴里·麦克唐纳问道,他淡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在弗拉特利鲜品食品店(Fratelli Fresh)一堆进口圣马力诺西红柿旁的走道停下。“不不不,哥们儿,真正的悉尼人不吃那种东西的。” 在麦克唐纳看来,鳄鱼肉是为游客准备的。悉尼人——也就是生活在这个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海岸、有着4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居民——爱吃一些世界上最可口的、具有创新性的美食。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摩登菜”(Mod Oz)运动在简单、新鲜的食材中融入亚洲的调味和欧洲的烹饪技巧,悉尼人被尼尔·佩里(Neil Perry)、唐娜·海(Donna Hay)、托尼·比尔逊(Tony Bilson)以及邝凯莉(Kylie Kwong)这些厨界明星给惯坏了。悉尼人讨论起“《悉尼先驱晨报》美食指南”(Sydney Morning Herald’s Good Food Guide)一年一度的厨师评定(从一顶帽子到三顶帽子),就像巴黎民众热烈争议《米其林红色指南》(Michelin Red Guide)最新评出的星级餐厅。他们去哲也家(Tetsuya)吃饭得提前做规划,预约位子,这里是由一位在日本出生的厨师经营,专做混搭风格的食物,经常被选入世界十大餐厅之列。 有相当数量的悉尼人会到类似弗拉特利鲜品食品店这样的地方购买食品,这是一个仓储式的食品商场,由巴里和他的兄弟杰米经营。这里一条条的通道两边放满了从世界各地进口的食物,比如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进口的栗粉,从西西里岛进口的盐腌小刺山柑,从昆士兰州来的菠萝,以及从西西里岛引种、在本地种植的“乔尼爱咬的”西红柿(johnny-love-bite tomato)。 大受欢迎的弗拉特利鲜品食品店(Fratelli Fresh)以气氛闲适的女高音咖啡厅(Cafe Sopra)和售卖城内最高品质的农产品和食物吸引着顾客。 作为悉尼149家餐厅的供应商,巴里似乎认识餐饮界每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告诉我,如果要找真正的悉尼味道,就应该去见见厨师尼尔·佩里。用手机打了一通电话,接着坐上出租车飞快地抵达环形码头,我在石池餐厅(Rockpool)靠窗的座位坐下,悉尼顶级厨师之一的佩里马上给我做了一顿由若干道海鲜组成的午餐。 五十多岁、头上扎着马尾辫的佩里不显年龄,80年代中期,他在位于邦迪海滩(Bondi Beach)的蓝水餐厅(Bluewater Grill)协助发起了“摩登菜”运动。佩里给我做了一些从未听说过的鱼:甜味蜥革寿司,接着是塞有大豆的煎蛋卷以及锯缘青蟹(一种昆士兰的红树林中盛产的甲壳类生物),最后是鱼片(一种深海鱼类,也叫南极鲳鱼)精心搭配泰式绿咖喱。 佩里非常关心过度捕捞的问题,与悉尼的许多餐馆老板一样,他拒绝提供罗非鱼、蓝鳍金枪鱼以及其他一些濒临灭绝的鱼类;他的菜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可持续捕捞以及人工养殖的物种。他说:“在澳大利亚,许多鱼都是用小渔船而不是拖网船来捕捞。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国家濒临灭绝的物种在这里会长得很好。” 悉尼最优秀的厨师都是饮食伦理的先锋,这或许是这个十年最为持久的烹饪传统。在悉尼最好的那些海鲜餐厅的菜单上,例如极佳的码头餐厅(Pier),这家由名厨格雷戈·道尔(Greg Doyle)开设的餐厅深入玫瑰湾(Rose Bay),都会列出捕捞的海湾和港口,以帮助消费者在点鱼的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魅力惊人的邝凯莉恐怕是世界上惟一提供可持续来源的中式家常美食的人。在萨里山(Surry Hills)永远需要等座的邝比利餐厅(Billy Kwong),邝凯莉的招牌菜是有机福建面条、令人称奇的回锅脆皮散养鸡,以及一系列精选的用生物机能酿酒法酿造的葡萄酒。 我发现,跟随直觉是了解悉尼的好办法。但也可能让你晕头转向。在人来人往的中国城、在灯红酒绿的英皇十字区(Kings Cross)、在时尚的纽敦(Newtown),我尽情享用着尼泊尔摩摩(momo,一种像馄饨或煎饺的食物)、印度的油炸蔬菜(pakora)、越南的牛汤河粉(pho)、马来西亚的罗惹(rojak,浇有辣椒酱的色拉)和冻咖啡(kopi ais)。特浓咖啡使我神清气爽地在萨里山和帕丁顿(Paddington)逛了一天,那些可以穿行的小区用洗瓶刷涂成猩红色和紫色,还种满了蓝花楹树;维多利亚时代的连排别墅装饰着用熟铁打造的阳台,让人觉得到了南半球法国人居住区。在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一片狭长的城市中心绿地,这里的标牌上写着“请从草地上走”,我跟着直觉走,结果却迷了路。 中国城的万寿菊餐厅(Marigold Restaurant)有非常可口的中式点心。 这里是澳大利亚最早的一块菜地,由当时的总督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开辟;这位总督带着第一舰队的11艘船、1400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囚犯)于1788年1月抵达了今天的悉尼港所在位置。虽然经历了狂风暴雨、船上恶劣的居住条件以及不断的鞭笞惩罚,这些人能从8个半月的航海行程中活了下来简直令人称奇。而他们的后代及其一代代的移民,能够建立起一座像悉尼这样充满魅力的城市,同样是一个奇迹。 很快,麦加利街(Macquarie Street)上段那优雅的建筑就被挡住了,我晕头转向地走在蜿蜒曲折的马路上,路两旁生长着叶似亚麻的千层皮树以及巨大的蕨类植物。我吃惊地发现,在巨朱蕉树上部的树枝上好像挂着许多裹在叶子里的大茄子。 作为一个以创意手法烹饪海鲜美食的时尚堡垒,石池餐厅(Rockpool)不仅吸引了悉尼人,也吸引了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客。 等等,我对自己说道,感觉自己就像是《魔域奇兵》里的一个群众演员:那些茄子在晃动。其实,它们是在一边扭动一边鸣叫,展开膜状的翅膀,炫耀着带钩的爪子和尖利的牙齿。原来,我恰好站在数千只灰头飞狐的下面,它们把植物园作为自己的永久营地,这会儿它们正在啃食着南半球最珍贵的植物。我开始意识到,悉尼是这样一种城市——在你喝完浓缩咖啡玛齐朵,走路不超过两分钟,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印第安纳·琼斯。 根据朋友希瑟的建议,我沿着弧形的海滨步行道来到“哈里的轮上咖啡馆(Harry’s Cafe de Wheels)”,霓虹灯招牌显示这家店创立于1945年。这家店在悉尼名气不小,看上去就像是那种你在世界各地的高速路两边经常看到的卖餐饮的卡车,车身花花绿绿全是手绘的壁画,还挂着帕梅拉·安德森(Pamela Anderson)、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罗尔夫·哈里斯(Rolf Harris)以及其他知名客人的照片。我排着队,四周是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的商人和两个晒得黝黑的英国游客。我点单后,日本裔的柜台小姐递给我一个老虎派(里面是牛肉,上面是土豆泥和糊状的豌豆泥,馅饼的凹陷处还装着肉汤)和一个短粗瓶装的冰冻姜汁啤酒。 我在几码开外的水泥台阶上坐下。前方是灰色的海军驱逐舰;头顶的澳大利亚国旗在风中飘扬;海湾对面是延绵起伏的市区天际线,最醒目的是悉尼电视塔的望台;一只美冠鹦鹉停在我头顶的街灯上。 好吧,我一边用塑料叉子在馅饼皮里挖掘,一边对自己说,这算是完美了。我在一处被原住民称为“乌鲁姆鲁(Woolloomooloo)”的海湾,大啖味道颇佳的英式派(我还在上面加了一些印尼甜辣椒酱)。派非常咸,皮厚馅料足,与微辣的姜汁啤酒搭配起来正合适。我把“哈里的轮上咖啡馆”加到了越来越长的悉尼独特体验名单上。或许这里的食物不是定义悉尼的味道,但毫无疑问,要找到比这里的老虎派更具当地特色的食物还真不容易。 说实在话,我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哪怕是点一杯咖啡,在这里你也得用完全不同的词汇:caffe latte(拿铁咖啡)得叫“flat white(纯白)”;要一杯Americano(美式咖啡),你得说要“long black(黑咖啡)”。显然,我得找个专家聊一聊。《延续下来的野餐》(One Continuous Picnic)是一本讲述澳大利亚动人的美食历史的书,其作者迈克尔·塞门兹(Michael Symons)跟我在一家名叫布恩·里卡多(Buon Ricordo)的餐厅吃意粉的时候,试图向我解释悉尼及其美食的历史。“长久以来,澳大利亚给外人的印象是:澳大利亚佬是粗鲁、爱喝啤酒、爱吃烤肉的土包子,而澳大利亚的食物就是两素一荤,” 塞门兹解释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移民,带来了意大利风格和其他欧洲风格的美食,这给我们的进餐过程带来了真正的活力和快乐。” 城市的游泳池:邦迪海滩的盐水游泳池。 这是一种我们正在经历的快乐,当服务生手脚敏捷地切开半熟的块菌鸡蛋扔进我们的意大利面时,我们的胳膊肘都快碰上邻桌的客人。在塞门兹看来,了解澳大利亚美食的关键,就在于要清楚澳大利亚是一个没有农业传统的国家。约6万年前,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游荡,但据他指出,他们是狩猎——采集文化,不事耕作。 “没有传统的束缚,我们可以随意尝试——尼尔·佩里这些厨师正是这么做的。”结果就像是塞门兹的书名所言,户外生活造就了朴实的大众菜式(澳大利亚汉堡和肉派)以及用新鲜食材制作的、有着独特澳大利亚风味的美食。我对塞门兹指出,不仅是这些,还包括我们当时佐餐用的产自雅拉河谷(Yarra Valley)的灰皮诺葡萄酒。 要想品尝具有当地特色的快餐美食,可以试一试哈里的轮上咖啡馆的美味肉派等 到目前为止,我所品尝过的澳大利亚美食带给我强烈的预感:如果真有一个惟一可以定义悉尼的味道,那应该是来自大海。毕竟,这是一个海港城市,这里的财富随着世界贸易的潮起潮落而跌宕起伏。 一大早在成箱批发鲂鱼、包曼 (Balmain Bugs,一种貌似太空七彩神仙鱼的龙虾)、巨型黄鳍金枪鱼的悉尼鱼市(Sydney Fish Market),我遇见了厨师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他给我大致介绍了情况。年轻时,摩尔周游世界,在伦敦里兹饭店当过学徒,后来一步步做到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现在,摩尔是顶点餐厅(Summit)主厨,这是位于澳洲广场(Australia Tower)47层的旋转餐厅,在这里,你能一边看着悉尼电视塔从你面前缓缓经过,一边把香槟茴香肉汁里的热鳟鱼仔放在舌头上让它慢慢融化。 我们坐在鱼市一个卖牡蛎的摊位旁,摩尔解释说:“悉尼最棒的地方在于,我们能轻易得到最棒的食物。在欧洲和美国,你可以吃到最棒的美食,但你得花大价钱。在这里,日常的食物都是高品质的;金枪鱼是不会用罐头装的,你点的炭烧黄鳍金枪鱼一定是新鲜的。在悉尼吃的就是纯粹的品质,吃的是自然之美,以及出产上佳美食的无污染的环境。” 悉尼岩牡蛎:这种味道鲜美、吃起来上瘾的牡蛎,获取了大海的精华。 说得好。经过几天的不停赶场吃饭,我还没吃到一顿不好吃的。在萨里山不起眼的泰式小餐厅“香料生活(Spicy I Am)”,我吃到了一生最好吃的青木瓜沙拉;在豪华的“本尼隆的纪尧姆餐馆”(Bennelong at Guillaume),在它貌似悉尼歌剧院鲸鱼状的拱顶下,大厨纪尧姆·普拉希米(Guillaume Brahimi)用来自蒙德格里·克里克(Mandagery Creek)农场的鹿肉以及来自塔斯马尼亚岛用青草饲养的牛肉做了生肉片,我从来没有感到食材是不新鲜的——用的都是经过精心准备、这里所能提供的最新鲜的原料。 现在我知道了,找到最完美的当地味道的那一刻,不会是在某家餐馆(排队等位子和高级餐馆绝对不是悉尼美食图景的全部)。当那一刻到来时,应该是在户外,就像是某种随性的野餐。 熠熠生辉的悉尼拂晓——来自港湾大桥下人行道的惊鸿一瞥。早早起来,可以捕捉到如此精彩的瞬间。 我坐在环形码头一处卖牡蛎的摊位,面前是一打经过熟练去壳的悉尼岩牡蛎,每一个牡蛎都有着小巧、优雅的外形,牡蛎肉沾着绿色,那是滤除掉的绿海藻。盘子的旁边放着一杯克莱尔谷(Clare Valley)出产的雷司令。太阳挂在大跨度的港湾大桥后面,金色的葡萄酒折射着它的光芒,仿佛光源就在酒杯里。 我看着小轮渡灵巧地离开码头,把悉尼人送回他们位于北部郊区的家。这似乎是完美的一幕——的确就是完美。毕竟,这里是悉尼的发源地。 当英国殖民者于两个世纪前抵达这里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堆堆约四层楼高的贝壳——那是欧拉人(Eora,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悉尼第一批长期的定居者)经过数百年的时间累积起来的。地点就是在这里,在坐落着悉尼歌剧院的本尼隆角(Bennelong Point),此时歌剧院贝壳状的拱形在太阳的余辉中变成了粉红色。 牡蛎每一滴亮晶晶的乳脂,都承载着咽下的一口塔斯曼海(Tasman Sea)的海水;它似乎让干白葡萄酒变甜了,而那葡萄酒本身就是南澳充沛阳光下红色土壤的纯粹之作。唇齿留香间,脑海中突然想到了什么。没错,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味道。不是丛林美味,不是肉派,也不是三顶帽子厨师的大作——尽管它们一定是美味的。在我看来,定义悉尼的味道只能是牡蛎和葡萄酒,大海和陆地,纯粹和简单。 如果幸运的话,对于这种味道的回忆,将会在未来某天让我再度回到这里。 |